周曉虹:變遷時代的觀察者
- 2017-03-08 11:39:00
- admin 轉貼

群學書院創始人周曉虹
01
2015年南京大學高研院十周年慶典時,舉辦了一個“學術伉儷”系列講座活動。周曉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對嘉賓。周曉虹是社會學教授,朱虹是管理學教授。報告廳擠滿了聽眾。
周曉虹和朱虹的學術領域有一些交集。比如,消費主義。周曉虹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《文化反哺: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》,就談到了中國家庭代際關系的變化與消費革命的興起。這本書,從萌發靈感到完成,整整用了25年的時間。
周曉虹調侃,如果讓講究效率的商學院教授來寫的話,可能只要兩個半月,但他認為很值。“從1988年到今天,這么長的時間、這么多的變動,才使議題的討論有了更寬廣的論域。用25年邂逅一個宏大的場面,非常有意義。”
文化反哺,是周曉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,用來指在急速變遷的時代,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學習的現象。這個詞近年逐漸從學術界走向大眾,已經成為一個流行概念。2010年,浙江省高考作文題目就是從角色轉換談文化反哺。

02
1985年,周曉虹的父親從部隊離休,領了一筆服裝費。父親給了他200元,讓拿去買衣服,但規定不能買西裝。在父親腦子里,西裝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征。周曉虹當時還在南開大學讀研究生,他背后雖然已經穿上了牛仔褲,但這200元錢卻嚴格接受了“投資人”的決定。
但三年后,1988年的大年初一,父親拿出一套西裝,讓周曉虹教他打領帶。“當時我就震驚了。父親也穿西裝?從來嚴肅的父親,竟然也為此向我請教。”周曉虹立即嗅到一些變化,這成為文化反哺概念的最初由來。這一年,周曉虹寫了《試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》一文,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。
1998年,周曉虹正在專心研究蘇南和溫州農村的比較,寫出了博士論文《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》。
這年里的一天,他聽到好友美學教授周憲跟人談電腦,談不過了,使出殺手锏:“不對,不對,我兒子說……”。周曉虹像觸電一樣,立即問旁人,聽到沒,他在說什么?大家并不以為然。
就是這句話再度給了周曉虹“社會學想象力”。他意識到,文化和知識的來源,判斷對錯的標準,開始從老一代到了年輕一代手上。“《文化反哺》這本書的副標題,‘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’,為什么是革命?因為兩代人的關系整個顛倒過來了。”
學富五車的美學教授的論證方式,證明了新的文化傳承方式的出現,甚至預示了一種全新社會的到來。在數字化時代,親代甘愿拜子代為師的現象,是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親子關系“顛覆”的特例。

03
周曉虹開始做一些案例研究。最先在南京選擇了7戶家庭,在北京“浙江村”選擇了2戶家庭,做田野調查和焦點組訪談。此時,人們對“文化反哺”的概念,還持“謹慎肯定”的態度。但調查結果出乎預料,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,父母向孩子學習已經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,“高知”父母也不例外。研究結果讓周曉虹相信:文化反哺這個概念是成立的。
此后十多年,周曉虹繼續做這項研究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南京和重慶五個城市做了77戶家庭的訪談。從食品、器物、行為方式、價值觀等各方面,對文化反哺現象作了全方位的解讀與分析。
在他看來,計算機是父母人生的“滑鐵盧”,原來“無所不能”的父母開始在計算機面前敗下陣來。手機,也體現了代際溝通的主導權,從上一代轉移到下一代。訪談寫道:幾乎所有父母都承認,在操作手機上,尤其是發短信方面自己極其低能,這構成了他們向子女學習的內容之一。
文化反哺是當今中國獨有的嗎?
周曉虹認為,中國的特殊性在于,作為一個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,經歷了30年的封閉、停滯后,突然劇烈轉型,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年長一代從“至尊”到“落伍”的過程幾乎是瞬時性的。因變遷導致的中國社會兩代人的差異之大是絕無僅有的。
《文化反哺》寫到三分之二,周曉虹被查出患了“腎癌”。他做好了一切準備,結果手術前一天檢查,核磁共振卻發現沒有問題。經歷了一次“生死”,他在書的后記里寫了一段很煽情的話:“爸爸,我終于寫完了。我用我的心血將我們父子因心靈的碰撞激起的一束情感的浪花,開掘成了一條汪洋恣意的大河!”

04
1990年代初,周曉虹注意到,在中國市場上,羞答答地出現了第一本以中產階層趣味為定位的《時尚》雜志,其基本主題是倡導中產階層“消費、消費、再消費。”而當時,在大多數人腦中,過度或超前消費仍是一種“錯誤”的觀念。
2001年,“想象力”豐富的周曉虹開始關注中國的中產階級。他是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學者之一。2005年,他在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南京和武漢五個城市做調查,為當時的中產階級畫了一副像:月收入5000元,有大專以上學歷,主要從事腦力勞動。他認為,在這五個城市,有12%的人達到這個標準,“現在覺得這個數字保守了。”
這一調查發布出來,引起一片質疑。幾周后,在Google搜索“周曉虹+中產階級”,有75400條消息。上海的一位白領把每一筆收支曬到網上:月入7000元,除掉開銷,每月只剩下200元。他質問周曉虹,我也算中產階級嗎!?而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標準,年收入6至50萬,也引起了爭議。
“當時人們確實懷疑中國是否存在一個中產階層。”周曉虹感到很疑惑,“改革開放快30年了,為什么很多人對中國存在中產階層持懷疑態度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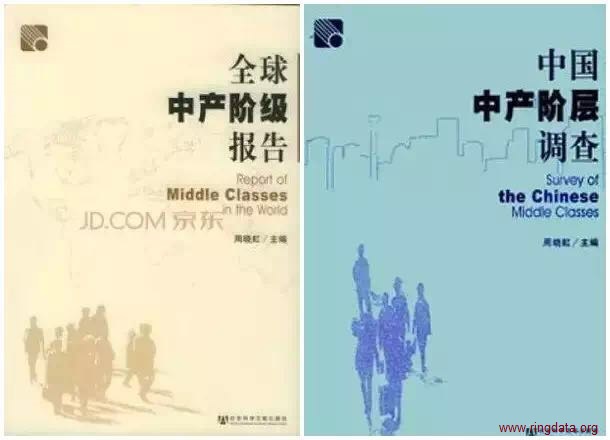
05
2005年秋天,周曉虹去印度開會,在德里的一個三星級飯店,跟大堂經理閑聊,問他是不是中產階級。大堂經理的月收入相當于人民幣1000多元,但卻自信地說,of course,I am middle class。接下來,經理的下一句話,差點讓周曉虹驚掉下巴:“你不知道嗎,我們印度是中產國家”。那一刻,他想起了100年前訪問芝加哥的韋伯,而孟買正像當時的芝加哥。
就是在這一年,印度號稱有7億中產階級。為什么兩國對中產階級的認識有那么大偏差?周曉虹想了很久,發現,中國人對中產階級的否認,可能源于對“middle class”這一詞的誤讀。
“中國人一向很注意這個‘產’,強化了人們對財產多寡的過度重視,而忽視了現代中產階級或者說新中產階級的職業特征。其實中產階級,就是從事腦力勞動的工薪階層,如果不受雇于人,除了自謀生計的個體戶,那可能就是資產階級了。而且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,官方多用“中等收入階層”一詞來替代。”
另外,周曉虹認為,人們對中產階級和中產社會產生了混淆。一些學者寫文章反駁,以中產社會的五條標準作為理由:第一,城市化率達到70%;第二,白領工作者大于或等于藍領工作者;第三,恩格爾系數降到0.3以下;第四,基尼系數保持在0.25至0.30之間;第五,人均受教育12年以上。顯然,對照以上幾條,中國遠遠不夠。
“我顯然不認為中國已進入了’中產社會’。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,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,‘金字塔型’不復存在,但目前還只是一只中間略大、底部更大的‘洋蔥頭’,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還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。”
周曉虹認為,中國中產階層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,盡管它像股市和樓市一樣,多少有些泡沫。但他的態度十分鮮明:一方面,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剛剛開始,具有相當的上升空間。另一方面,從不幻想中產階層的成長能夠解決全部的問題。

06
周曉虹曾下鄉插隊兩年。在農村時,他很喜歡寫東西,小說、詩歌都寫,創作熱情很高,在田間地頭宣傳隊要上臺,他五分鐘就能寫出一首詩來。1977年,恢復高考,670萬人參加考試,錄取27.8萬人。周曉虹考取了南京醫學院醫學系。他沒有考中文系,“那時候傻乎乎的,覺得文學家都從醫生出來的,郭沫若、魯迅,所以就想干脆學醫吧,就這么簡單。”
進了醫學院,他還是“不務正業”,繼續寫小說,鼓搗傷痕文學。年紀稍大,理性漸長,發現當年寫的小說,就像調查報告,已不能卒讀。于是放下小說,研究起社會學。“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,一切百廢待舉,再說我一看那時領頭的又是費孝通先生,我就考到南開去,把自己的一生都改過去了。”
1990年代,全國上下涌動著一股野蠻的活力,高校教師紛紛下海。1993年周曉虹碰巧到海南授課。先期下海的南開和南大兩所學校的十位朋友來接他,十輛豪華轎車一字排開,讓他隨便挑,想上哪輛上哪輛。周曉虹上了一輛最豪華的車。半路上,十數位武警端著沖鋒槍跳出來,喝到:把手舉起來。朋友說別怕,估計是“出事了”,例行檢查。第二天報紙報道,海口一家銀行被搶走50萬元,打死兩人。
下了車,一行十幾人向燒烤城走去。領頭的朋友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,像黑社會老大,兩排女服務員齊刷刷地鞠躬,大喊“請”。朋友說,看到了嗎?這就是金錢的力量。周曉虹現在還能記得朋友當時的表情。
那時,他的月薪是一個月150元,三個人住學校的宿舍里。朋友們的月薪都是5000元以上,還有原始股。朋友說,干脆甭回去了。周曉虹還是回去了。1992年,周曉虹給儀征化纖寫了一句廣告語:“儀征化纖,與世界共經緯”,得到一萬元報酬。后來那句廣告語出現在各地的機場碼頭。當老師能維持興趣,還能掙點外快,過得比較寬裕。朋友的飛黃騰達,沒有給他太多刺激。
“如果換種生活方式能讓掙的錢以幾何級數增長,我也許會放棄興趣;但如果只能以算數級數增長,當然興趣第一。”周曉虹說,“其實商人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,我跟他們一樣,只是角色不同,Calling(天職)不同。我在課堂上的滿足感也很強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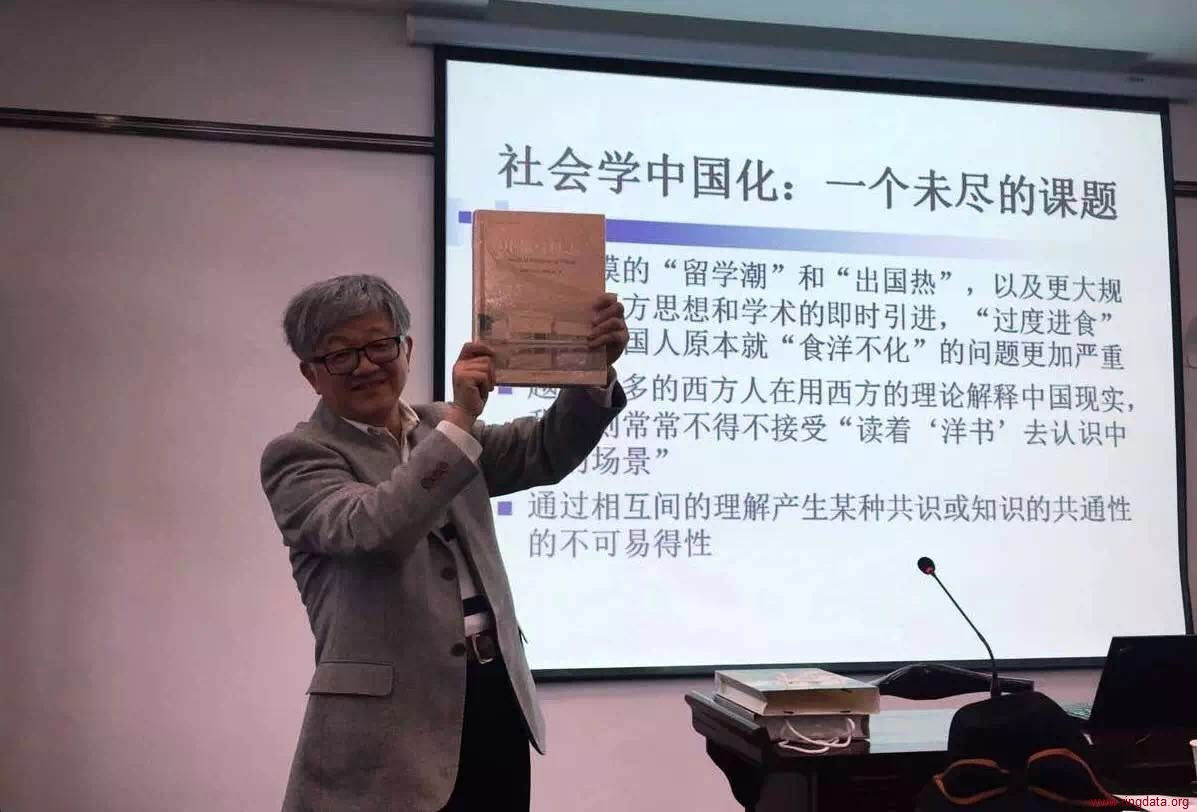
07
在南大的一次學術午餐會上,新聞系教授潘知常笑言:周曉虹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遺憾。
在周曉虹看來,遺憾其實是有的。“當你用25年完成一本書,而你又有許多研究興趣時,你會感到以生之有涯對知之無涯,非常悲涼;我一生想寫很多書,而留給你的時間只夠寫兩三本好書,怎么會沒有遺憾?

